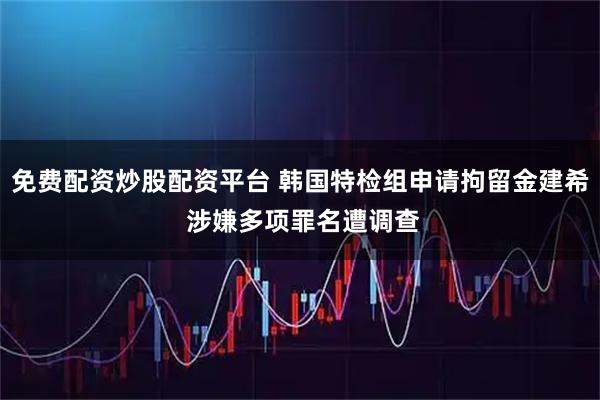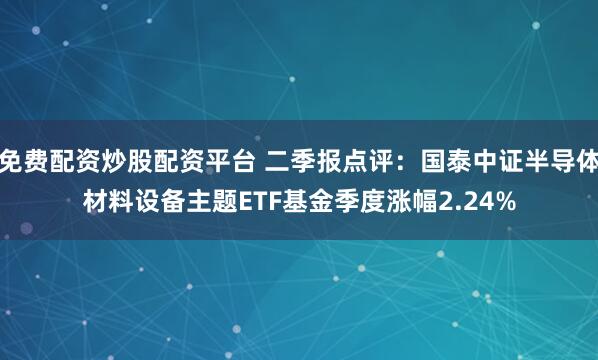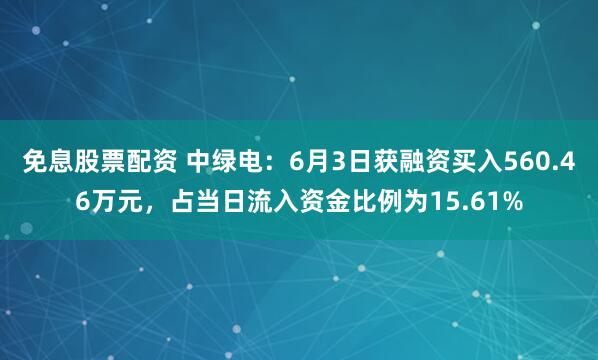D AJIA LILUN免费配资炒股配资平台
贵州日报
2025.8.13 7版
屯堡文化是伴随着“贵州建省”与生俱来的血脉,是承载着宏大国家战略,具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重大时代价值的文化瑰宝。8月9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五期)”在贵阳孔学堂开讲。多彩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继焦教授围绕“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还是边缘化”主题,聚焦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贵州屯堡文化、如何看待贵州屯堡文化的中心性或边缘性这一主要内容,深刻阐释了屯堡文化演变的结构功能及屯堡文化的重大国家价值。本报特将讲座内容进行摘录发表,以飨读者。
展开剩余89%“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还是边缘化”
贵州屯堡文化演变的结构功能分析
张继焦/ 文
张继焦,多彩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现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主要学术专长为经济社会学(包括企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经济社会转型等)、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等。
中国历史上的边远地区,是在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疆域演进过程中建构和发展,并不断向外扩展出来的。就自然地理空间位置的相对性而言,自然意义上绝对的“中心”和“边缘”并不存在,更不存在所谓的边远地区边缘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大背景下,通过分析贵州屯堡文化演变的结构功能发现:贵州屯堡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无论结构功能怎么变迁,都在推进边远地区的中心化。明朝时期,军屯卫所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了边远地区对中心地区的归附;清朝开始到20世纪末,屯堡人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持续提升着边远地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21世纪以来,贵州屯堡文化迈向现代化发展阶段,借助文旅融合正在逐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经典游学线路
Dajialilun
“中心—边缘”或“中央—边疆”关系的探讨
一些国外学者将长城视为区隔华夷的历史分界线。实际上,自先秦以来,我国历代多以长城为界,实行内外分治。但至清朝,康熙帝做出“废止长城”的重要决定,主张不再修理长城,不再派兵驻守,长城南北“无分内外,视同一体”,此举突破了“华夷之辨”民族观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使“华夷一体”的“大一统”民族观正式确立。“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点对传统的“中原中心观”有所突破,为国际学界开展中国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究其本质,“长城内外有别”与“长城内外一家”两种观点属于对立关系。而“新清史”学派“边疆是边疆,中原是中原”等极端观点更认为,清王朝是由内陆亚洲(边疆)和中国(内地)两部分组成的,边疆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与中原文化或者中心文化并没有交融,边疆具有自己独有的民族特性,不具有中(原)心文化的特性。
贵州屯堡文化产生于历史上的边远地区,很多时候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孤岛”。如何看待贵州屯堡文化的中心性或边缘性?我们应该采用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来分析中华文明史、考察历史上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分辨区域历史与民族历史和讨论族群等问题,而不能过度强调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异质性,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特性,割裂地而非统一地去观察边远地区及其区域文化。关于“中央—边疆”关系,近年来我已发表了三篇论文,反驳“新清史”学派有关观点。我们与“新清史”对话,加强探讨边疆地区的中心化而不是边缘化问题,将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ajialilun
贵州屯堡文化的基本情况
600年的屯堡,600年的故事,600年的沧桑。贵州屯堡文化与卫所的分布基本一致,主要分布在安顺市的西秀区、平坝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贵阳市清镇市卫城镇、花溪区青岩镇,毕节市七星关区,六盘水市盘州市双凤镇,黔东南自治州黄平县、镇远县、锦屏县,黔南自治州福泉市,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等地。一般认为,贵州屯堡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明代汉族移民文化的活态保存与多元融合,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石头建筑、明代服饰遗存、地方方言传承、地戏表演艺术等多个维度,并在600年间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贵州省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七个方面对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行了界定。2023年7月,贵州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明确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将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列入“四大文化工程”,屯堡文化研究推广工作起势良好、进展明显。
Dajialilun
贵州屯堡文化演变的结构功能分析
屯垦戍边:贵州屯堡文化的产生及其军事结构功能。以结构功能视角观测贵州屯堡文化的演进,首先要了解中国历史上屯田制度的发展,以及明朝初年为了统一西南疆域,平定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的割据势力所开展的“调北征南”战略部署。以此为始,追溯贵州卫所军士的来源及卫所制度产生,从而探明贵州屯堡文化形成阶段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朱元璋平定川渝之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成为元廷在南方最后的势力,对于明朝廷七次招降拒不接受。然而,欲取云南,必经贵州。当时的贵州,明朝廷依旧采取的是元朝的地方管理机制,在贵州广阔的民族地区采取“怀柔”之策。在“各安其生”的政治招谕攻略下,以水西安氏土司等为代表的几大土司带头归顺,带动众多地方势力的归降。明军统一了今天贵州的大部分区域,地方势力被纳入明中央王朝政治体系。为保证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忠诚,明军在贵州设立了贵州卫和永宁卫。卫所开始在贵州大地上建立。为保证进攻云南行军路线的畅通,明中央王朝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黔之腹、滇之喉”一带新归顺地区的统治,借鉴中国历史上对边远地区所采取的屯垦戍边的经验,结合原有的军屯实践,将屯田戍边灵活运用于贵州地区,以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和行军后方稳定问题。至此,军屯体系逐渐在贵州落地,贵州卫所基本成型,贵州屯堡文化产生的军事架构初步建成。这些军屯卫所所需的一切功能性结构十分完备,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严谨制度、独立结构和完善功能的运行系统,发挥着守御和稳定边远地区的功能,推动了边远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归属,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推进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军民一体:贵州屯堡文化发展时期的结构功能变化。600年的坚守与发展,贵州屯堡文化未被时间抛弃,一直在贵州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和自身强大的包容性下不断地自我扬弃。在屯堡人亦民亦军的身份传承方面,从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宏大的政治结构看,清朝及其后时期的屯堡已经不再是维持中央王朝稳定和统治边远地区的军事力量。尽管失去了军事身份,屯堡人并没丢掉曾经的意志和固守,反而以一种亦民亦军的身份继续存续着。从边远民族地区的中观结构考察,屯堡文化在和周边其他文化的互动与博弈中不断传承。从屯堡内部的微观结构观测,除了强大的内聚功能,还有一套持续存在的、像军队一样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以及与之相适配的军人精神。在屯堡文化的家国意识方面,卫所制度形塑下的贵州屯堡文化的家国意识,就是国家意志通过军屯制度由上而下的传达,并巩固于基础社会而形成的民众共识。从供奉“天地君亲师”到地戏等各种集体仪式活动所强化的群体归属感,都说明贵州屯堡文化自其形成之始就包含着强烈的国家意志和集体意识及由此展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家国意识已深入每个屯堡人的心灵和基因。贵州屯堡文化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又有彰显国家价值对周边民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守正创新:贵州屯堡文化现代化及其结构功能转型。从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形态看,贵州屯堡文化更像是600多年来,明中央王朝主流文化进入贵州后与当地文化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活的文化样态,以一隅之光彰显着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壮阔历程,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发展。今天,这种活的样态依然继续存在,并以现代化的方式推动着贵州屯堡文化融入现在、走向未来,持续地塑造着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不断实现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的现代化转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进边远地区的中心化。从贵州屯堡文化的文旅开发看,其超越了地理位置的约束、历史传承的局限,成为全世界解读和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鲜活的实践,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民族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屯堡文化旅游为代表的现代化创新发展模式改变了贵州屯堡文化原来相对封闭的结构,以一种开放的旅游目的地形态融入现代化的进程,卫国戍边的政治功能和自我维系的社会功能拓展成了旅游功能。结构功能的转型,并未造成贵州屯堡文化的消解,贵州屯堡文化中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其形式在保护、传承和创新中与时俱进。在守正创新的前提下,通过对贵州屯堡文化的再创作、再演绎,不断将传统与现代有效结合,引来了越来越多人主动地了解、关注、传播。
Dajialilun
屯堡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具有重大国家价值
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贵州屯堡文化?过去,屯堡文化长期被看作贵州甚至安顺一地的地域文化,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人类学、民俗学等层面。通过大力推动,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在工作中深化了对屯堡文化的认识:屯堡作为明朝守卫、开发和管理西南边陲地区的重要依托,与明朝重修长城一样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屯堡文化是随着明代贵州建卫所与生俱来的文化血脉,不是一般化的地域文化,从历史和现实看,都具有重大国家价值。
归属“中心”:大一统中央王朝建构中的贵州屯堡文化。历史上边远地区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文明力量较为弱小,很容易被中央王朝吸纳和统辖。但中央王朝要实现从统一到统治的长期性,维护其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地位,就得打破边远地区在地缘格局中存在的边缘性。如此,边远地区的军事化就成了中央王朝不二的选择。因此,贵州屯堡文化的建设早期是一种军事结构,承载着的是中央王朝的军事功能和统治功能,军事实践的背后是国家强硬的权力意志,展现出的是“中心”对所谓“边缘”的吸引和所谓“边缘”对“中心”的归附。军屯制度的建立,增强了边远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尤其表现为军事力量带给当地文明在记忆上的国家力量震撼以及权力从属上的国家认同。
连接地方:融入边远地区的贵州屯堡文化。随着所属中央王朝统治的结束,贵州屯堡文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融入外部世界,打破固守的卫所,转向开放的屯堡,为传统军屯聚落带来了更多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中心文化通过贵州屯堡文化影响边远地区文化,向边远地区输送着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价值,又为中华文化汲取着边远地区“小文化”的营养。贵州屯堡文化仿佛一体和多元之间的一根血脉纽带,壮大中华文化,哺育边远地区文化,也实现了自身的茁壮成长。贵州屯堡文化连接下的边远地区“中心化”过程,是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文化加强连接的过程,是边远地区的地方社会日益告别较为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与外部世界发生多重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边远社会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强、中心化特征更加突出。
迈向现代:推动贵州屯堡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和国家在边远地区推动的文化建设、乡村振兴,不仅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和网络压缩了物理空间上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的现实距离,也在情感上拉近了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的心理距离。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强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进程,增强了边远民族地区向国家中心地区靠拢和融合的向心力。现代化时期的贵州屯堡文化作为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地区文化结合的历史延续,既有边远地区的特殊性反映,也有中心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国家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正是贵州屯堡文化在历史和现实、守护和创新、中心地区文化和边远地区文化之间的结构功能张力,才能呈现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与不变之间的独特魅力。
主持人语
石峰(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屯堡文化历经600年风雨,是一部镌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印记的“活”的明代史诗,是贵州大地珍贵的文化瑰宝。屯堡的赓续发展,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在西南边陲开枝散叶、融汇创新的历史智慧。近年来,贵州将屯堡文化纳入“四大文化工程”予以重点研究推广,并出台《贵州省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正是对这一文化所蕴含的国家价值与时代意义的深刻把握与主动作为。张继焦教授多年来持续关注屯堡文化,多次深入贵州调研,他认为,贵州正在实施的屯堡文化研究推广工程有关研究成果与其研究结论一致。
张继焦教授的讲座从深刻的历史纵深和宏阔的国家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及其变迁的核心动力,这一变迁深刻地推动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进程,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生动样本。
张继焦教授除了探讨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而不是边缘化问题,澄清某些错误观点之外,还鲜明地提出屯堡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承载着重大国家价值;贵州屯堡文化在良好的保护下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创新,必须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结起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化对屯堡文化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认识,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策划制作 陈翔
编辑 徐吉欧 王瑶
二审 杨春凌 韦一茜 王塬钧
三审 张莹免费配资炒股配资平台
发布于:北京市富华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