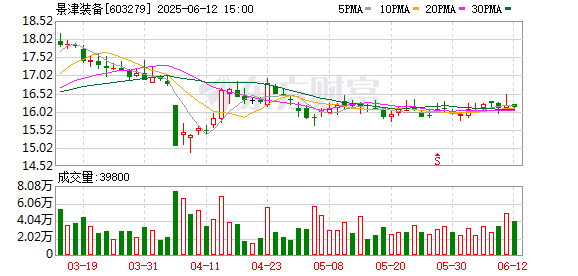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幽谧的展厅里,一张印在展板上的黑白照片,在明暗交错的光影中静静悬垂——赵一曼坐在高背藤椅上,怀中的稚子宁儿天真烂漫。
照片里透着的安宁,永远停驻在1930年的某个时刻,那时哈尔滨的丁香还未沾染硝烟。然而,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这位母亲便决然奔赴抗日战场,她怀中的孩子已托付给亲人。
展厅内的灯光,将参观者的身影拉得漫长,长得仿佛能一步跨回1936年那个血色的黎明:在珠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外的刑场上,赵一曼高唱《红旗歌》慷慨就义。那颗穿过她胸膛的罪恶子弹,最终在历史的天平上,化作了审判侵略者的千钧砝码。而那张母子合影,终成为穿越时空的见证:一个母亲最柔软的牵挂、一位战士最坚硬的骨头、一名党员最忠诚的信仰,原来可以如此完美地熔铸成同一个灵魂。
黑土与信仰
也许有人还不知道,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淑宁、李一超,本是四川宜宾的一位富家千金。1905年,当这个川南女孩呱呱坠地时,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她会跨越千山万水,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追寻信仰之光。
展开剩余87%翻开赵一曼的人生履历,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6年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再到1927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些在进步书刊上读过的真理,渐渐化作她血脉里奔涌的信仰,串联起她革命的足迹。
1928年冬,当党组织安排赵一曼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工作时,她已经身怀六甲。妊娠反应折磨着她的身体,丈夫陈达邦虽万分不舍,但也尊重妻子的选择:“党的决定,不能还价。”这句话,从此成为她一生的注脚。
回国后,赵一曼辗转于湖北、上海等地。当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撕裂了东北的天空,党组织的一声召唤,赵一曼便只身北去。1932年的风裹挟着江南烟雨,赵一曼从上海码头登上了轮船,经大连前往沈阳,后到达哈尔滨。从此,赵一曼将在这片沦陷的黑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浇筑一座不朽的丰碑。
彼时,哈尔滨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骄横跋扈的日伪军警宪特乘电车从不买票,甚至对电车工人拳打脚踢,工人们却连最基本的工资都被克扣。
1933年4月,当又一名电车工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时,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时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连夜组织电车工人开会,她以工人的觉醒为纸,以罢工的口号为墨,将入党时的誓言一笔一画重新描绘——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一夜之间,揭露日伪统治罪行的纸张贴满了大街小巷。一辆辆瘫痪的电车仿佛变成锁链,紧紧缠住侵略者的手脚。
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赵一曼用知识分子的智慧、革命者的勇气、党员的赤诚,在北国播撒下抗争的火种。当第一辆复工的电车重新出发时,叮当叮当的车铃声穿透云霄,仿佛一名战士对祖国最炽热的告白。
在血色浸染的1933年,赵一曼将汲取的知识、立下的誓言,都化作了满腔爱国情,写下了那首流传后世的《滨江述怀》:“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这些诗句,如同黑暗中点亮希望的火把,从哈尔滨一直燃烧到珠河县的密林深处……
1934年,操着南方口音、身体瘦弱的赵一曼来到珠河县。夜晚,山风掠过密林发出簌簌声响,仿佛在问这个倔强的灵魂:割舍襁褓中的幼子,投身于烽火连天的东北抗日战场,值得吗?而正是这份“誓志为人不为家”的忘我抉择,让赵一曼在东北雪原上挺过了更残酷的考验。
赵一曼心中的信仰之火,在珠河县终成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她鼓舞,拿起武器,成为最勇敢的战士。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危难中前行,用生命守护信仰,以忠诚铸就丰碑。
红装与白马
四季流转,赵一曼早已将巴蜀的温婉淬炼成北疆的坚韧。她的足迹踏过三股流的密林、铁北区的雪原,像一簇不灭的火苗,在日军的围剿中顽强地跳跃。
初到铁北区时,战士们并不知道这位瘦弱女子的姓名。彼时,赵尚志在珠河一带已是威名远扬,两人在抗日战场上肝胆相照,赵一曼的名字便是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
一次,战友朱新阳问她:“你为什么叫赵一曼呢?”赵一曼答道:“我喜欢‘一’字,所以给自己起的名字都带个‘一’字,一超,一曼,意思指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绝不改变……”
这个名字,自此化作了一面精神旗帜,在历史的天空猎猎飘扬。
在赵一曼屡次创下的战果中,1935年的关门嘴子伏击战可谓光辉的一页。
这场战役源于赵一曼得到的一则情报:一队日军从珠河县出发,前往铁北区关门嘴子一带“讨伐”。
赵一曼召集农民自卫队,部署了精密的作战计划:拿快枪和土炮的队员埋伏在最前边,攻击敌首;拿大刀和长矛的队员埋伏在后,截断敌人后路,夺取武器。
风送来远处马蹄声的碎响,似乎每一片树叶都在等待她的号令,准备谱写新的传奇。
就在敌人走近伏击圈时,枪声在密林间炸开,日军指挥官如枯叶般从马背上坠落,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像被惊散的蚂蚁,扔下枪支、子弹,落荒而逃。
此后,这支由赵一曼组建的农民抗日武装,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不断向日寇出击。
1935年,赵一曼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委员。最初,许多战士都十分疑惑:这个南方女子瘦弱的身躯,能经得住这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吗?
赵一曼不仅用实际行动打破了所有人的疑虑,就连敌人都对她“赞叹不已”。
一次,在侯林乡的山谷里,部队被日寇重重包围,激战一天一夜也未能突出重围。千钧一发之际,敌人背后突然传来枪声,只见赵一曼骑着白马,率领援军,如利剑般刺入敌阵。她手中的双枪,射出愤怒的火焰,把敌人的包围圈烧出一个缺口。日寇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阵脚大乱,节节败退。
战后,日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比最勇猛的战士还要令他们胆寒。交通员从白区带回的报纸上印着“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字眼,并描述她是“红衣女将”“双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将她与赵尚志一同列为北满地区需要剿灭的“大匪首”。
然而,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红装白马女政委”,却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
一次战斗中,赵一曼左臂中枪,在侯林乡西北沟老于家窝棚前养伤。可是叛徒的出卖,让这个最后的庇护所也失去了安宁。1935年11月22日,枪声划破了山林的寂静,在近两个小时的殊死抵抗中,赵一曼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直到腿部中弹昏迷。鲜血染红了积雪,在这片她战斗过的土地上留下了鲜红的印记。
北风呜咽,带走了这位巾帼英雄的自由,却带不走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精神火种。她的被捕,不是抗争的结束,而是又一面旗帜的升起—这面用忠诚与勇气织就的旗帜,将继续在东北雪原上飘扬。
赵一曼和儿子宁儿(陈掖贤)的合影 资料图
母亲与牵挂
如果不是日伪当年留存的档案,很难想象被捕后的赵一曼究竟经历了什么。但可以想见的是,敌人的监狱,一定冰冷得深入骨髓。
主要负责审讯的日寇大野泰治,瞄准了赵一曼最脆弱的部位,故意用皮鞭狠狠抽打她的伤口,鲜血浸透她破碎的衣衫,黏在伤口上,又被下一鞭硬生生扯开。
赵一曼咬紧牙关,不肯屈服。见酷刑无效,大野泰治等人用“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魔鬼之下流、变态、残暴、狠毒”的残忍手段对赵一曼继续拷打:她被高高吊起,拔掉手指甲,凿断牙齿,电刑器灼透五脏六腑……
然而,赵一曼仍拒不交代党的秘密,只留下一句坚定的誓言:“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多年后,大野泰治,这个曾经残暴的施暴者,在忏悔时表示,自己最终被赵一曼顽强的意志所折服。
因多次受刑,赵一曼腿部伤口恶化,生命垂危。日寇由于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并不想让赵一曼就这样死去,于是将她送至哈尔滨市立医院(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治疗,还在病房外增派守卫。但日寇不知道的是,真正让他们无奈的,不是这个虚弱的身躯,而是她心中那比刀剑更锋利的力量,那是用信仰淬炼的灵魂。
住院期间,赵一曼以革命者的智慧,悄然瓦解了敌人的防线——她将日寇在中国的暴行、百姓遭受的苦难,一一写在纸片上,偷偷交给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在她的感召下,两人坚定了反满抗日的决心。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和韩勇义成功帮助赵一曼逃跑。6月30日清晨,天边泛起微光,就在赵一曼以为这光亮将冲破命运的黑暗时,远处,敌人的追击声却如惊雷般响起。那近在咫尺的自由,终究被碾作尘埃,赵一曼再次被捕。
此后,赵一曼被关押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再次受到日伪警察灭绝人性的摧残。
敌人始终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不肯屈服。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折磨,恰恰是对“甘将热血沃中华”的铮铮誓言的最好诠释。直到最后一刻,赵一曼仍用破碎的身躯证明:对党的忠诚,比死亡更坚硬。
一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敌人决定将赵一曼押送至珠河县公开处决。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这位年仅31岁的母亲,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行刑前,赵一曼在火车中,诉说着最温柔的诀别:“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陈掖贤)的绝笔信,后由陈掖贤誊写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图
月影孤守,阴阳两隔。数千里外,她的丈夫再也等不到妻子的消息,哭泣的孩子再也无法得到母亲的亲吻……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赵一曼没能成为一个寻常的母亲,可她用生命为千万个孩子换来了不必在敌人刺刀下战栗的明天。
多年后,宁儿终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读到了母亲的这封遗书。如今股票配资风控,它已然成了最锋利的刀,剖开历史的真相,让人们看见那颗仍在跳动的心脏。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字句,不仅在岁月流转中舒展成最温柔的叮咛,更是对民族觉醒与复兴最永恒的牵挂。
发布于:北京市富华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票配资风控 香港自保保险公司增至6家
- 下一篇:股票配资风控 组图|艺术后湖好打卡